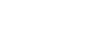点击一下,解锁更多精彩小说
送走医生后穆凤兰又回到房间,漠北已经睡熟了,屋里很暗,窗帘紧紧地拉着,壁灯发着橘黄色的光,孩子的手蜷在心口,嘴角紧紧地抿着,眉头也紧紧的蹙着。
把挡在她额头上的头发拨到身后,露出一张秀气的脸,真像啊,和她妈妈真像,唉,穆凤兰叹息,‘总皱眉头干什么呢’,都长得那么漂亮了,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呢?
唉,也难怪总皱着眉头,自己到底不是她亲妈,这么年轻该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纪,不论外人对她多好也得先学习察言观色,这是人性本能。
十年前
她第一次见到漠北是在她妈妈的葬礼上,小漠北抱着妈妈的遗像从储钱罐里掏葬礼钱,那天她哭的比她还像个孩子。
她要带她走,漠北抱着遗像蹲在角落里,人群散尽,最终点了头,从那开始莫北的莫多了三点水,成了漠北,刚来时她睡不踏实,床头要点盏灯。
掖了掖被角,再次叹了口气,小北快23岁了,她和小絮有个约定,要是他们生了一男一女,就在23岁办婚礼。
定下约定的是她和小絮,和她一同长大穿一条开裆裤的小絮,她总忍不住想,要是那年她没搬家没离开,或许小絮就不会选择那么极端的方式离开,要是当年她能多打上几个电话发上几条信息,即便是在过年这样的日子,即便是为了寒暄。
可那时候她怕了,从万千宠爱到家道中落,她怕别人同情的目光,怕那时自己的困境在别人眼里变成笑话,尤其是发小的同情,再等等,再等等吧,等她稍稍翻过身。
几乎她都能想到,小絮那时坐在电话的彼端,呆呆的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一言不发地挂断了电话,是不是,自己也是加剧她死亡的帮凶?
小絮的日记里写着,“我和凤君好像不光是在不同的地方,也在不同的时代,她走的很快,我却走的很慢,好像隔着大西洋,时间和距离都是罪犯,手机也是,它只能播出号码,却不能代我说出我想她了”
直到穆凤君的生意好了,她兴高采烈的打过去,却被告知小絮不在了,电话那头稚嫩的声音告诉她,“阿姨,您是妈妈最好的朋友,您要来参加她的葬礼吗?”
最好的朋友?她觉得惭愧,觉得无地自容,她模糊地记得小絮说过:“凤君,我好像病了,我最近总无缘无故的想哭”可那时她忙着多睡5分钟,并没有认真的听她说话。
在越来越发达越来越顺心的时候挂断了自己好友的一遍遍的电话,忽视了一个个饱含着真心的祝福讯息,她凭什么标榜自己是她最好的朋友,凭什么以她最好的朋友身份心安理得的自居?!
这个悲剧还得加上小絮的丈夫,他算得上是这个悲惨故事的主角了。
爱情、友谊、不懂事的女儿将这个女人逼上了绝路,一条活不下去的死路。
不是她不够坚强,不是她不够勇敢,而是他们做的太让她伤心了,伤心到让她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抑郁症,直到再也无法维持。
她把小北带回家,发誓会像小絮那样对她会给她所有她能给的爱,包括那场娃娃亲一定会有的。
况且这些年小隅和小北看着不是也都挺喜欢的?
那层窗户纸她会在适合的时候捅破的,穆凤君打开了门,那孩子还在熟睡,那场娃娃亲、泗水湖畔的春天里的婚礼最终一定会有的,看着吧、一定会的!
穆凤君关上了门,漠北还在熟睡,眉毛又蹙了起来,腰两侧的手重新蜷在心口。
………
闹钟响起,漠北沉沉的打了个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