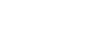点击一下,解锁更多精彩小说
的青青绿绿的草和红红白白的花儿。
夏天和秋天里,到处都是鸟儿、知了的叫声和小心谨慎就能偷到嘴里的桃子、杏儿等等水果。
冬天里。也有好玩的,大人把草们收拾到一起。垛成一个又一个的大草堆,我们就钻进去玩“趴猫儿”。
运气好的日子里,我们甚至能捉到一只刺猬或者看到一只顾不得放出臭屁而仓皇逃窜的黄鼠狼。(我们叫它“骚水狼子”)
可以想象,那么一个地方,应该是孩子的乐园。
我准备在《童年的乐园》里详详细细地写出我们在那个园子里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时光。
村西的张家老茔,模样和那大园子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些松树、柏树、柞树,(我们叫它橡子树,它长一种椭圆形的外面有带刺的壳儿的果子,和栗子差不多)少了柳树和各类果树,杂草里多了荆棘,多了艾蒿,多了小野物等等。
我和大平和大姐都是小学、初中的同学。
大姐虽然比我大三岁,但是因为三婶身体常年有病,需要她照顾两个弟弟,所以,她一直到了十岁,才和我一起上了学。
至于大平,则是因为七岁那年爬大杨树掏小山鸦鹊,从树上掉下来摔折了腿,错过了两年的入学时间,只好委屈着一拐一拐地与我同学。
没上学之前,我们四个人除去在老奶奶的老屋前玩摔泥娃娃玩老鹰捉小鸡等等游戏外,(关于童年的那些游戏类的记忆我准备在《童年的游戏》中详细写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个大园子和老茔里度过的。
上学之后,我们课余和星期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村西的沟壑里和村南的小山丘上以及村东的望不到边的庄稼地里度过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母亲已经开始强制我们挖野菜、拾草、刨药材了。
对比那种纯粹的玩耍,这种种的劳动十分的令人讨厌。
可是,我们惧怕母亲的斥骂和巴掌,于是,只好委曲求全,费些力气,把篓子弄满,然后,学着生产队长的腔调,大声吆喝道,歇歇了!哎,歇歇了!!
遇到费了些力气仍未填满篓子而又特别想玩的时候,我们就折几根绵条,支在篓子的底部,把野菜或者野草轻轻摊在上面,然后,玩去。回到家,把篓子朝母亲眼前一送,说,篓子满了,我回来了。
――
小的时候,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背后里叫大平“跟脚子”,认为那是大人们看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才那样叫他。
直到十五、六岁了,才知道“跟脚子”不是好听的名儿,和我后来知道的“拖油瓶”一样。都是对跟着母亲在父母成婚那天出现的孩子的蔑视之称。
大平是我二奶奶嫁给我二爷爷时就带着的孩子。听我奶奶说。那年,大平两岁。
我奶奶是我二奶奶和我二爷爷的媒人。
我二奶奶在娘家村里和一个有妇之夫相好后怀上了孩子,六、七个月了,她的爹妈才发现了。那年头流产的手段不多,而我二奶奶又消极对待吃药、爬树、跳墙等等爹妈想出来的种种办法,让大平在她的肚子里继续茁壮成长。
二奶奶快临盆的时候,爹娘逼问出了孩子是谁的,于是。爹娘和她的兄弟们把她送到了那个男人的家里。
那男人的一家因了理亏,只好侍候了二奶奶的月子。
那时候,建国已经六年,新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不准娶妾,那男人的几个舅子后来忍不下去了,跑到姐姐家,把我二奶奶和大平装在一个大麻篓里抬到了二奶奶娘家的门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