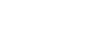点击一下,解锁更多精彩小说
我叫林野,名字在族谱里是破土的笔画。2007年10月的一天,接生婆把我裹进浸过艾草的襁褓,窗外的梧桐正落下第一片金黄——后来才知道,那片叶子的脉络,早已在我掌纹里长成了回乡的地图。此刻二楼的中央空调送出人造凉风,我却听见记忆深处有犁铧划破泥土的声响,像某种古老的密码,在每个月升时分破译着存在的真相。
六岁半时跟着父亲去田地里干农活。铁制的犁头在手里沁着寒意,木柄上留着祖父掌心的弧度。父亲说:"扶耧要像抱刚出生的羊羔,太松籽会撒歪,太紧地会疼。"我盯着耧斗里滚动的麦粒,它们在晨光中闪着珍珠般的光泽,忽然发现每粒种子都是时间的胶囊——埋进土里的是去年的收成,长出的却是明年的希望。当耧车在田垄间划出三道平行的痕迹时,原来土地早就懂得:有些相遇不必相交,却能在岁月里共同生长。
我蹲在田垄上把耧斗里的麦粒往指缝间漏,看它们滚成金红色的细流。"爹,"我忽然揪住父亲裤腿,"为啥耧脚踩过的土要凸起来?像大地长了青春痘。"父亲正弯腰调整耧铧角度,闻言直起腰时犁头磕在土块上,惊飞了两只啄食的麻雀。他抹了把汗笑:"你把种子当娃娃哄睡,不得给盖层软和的被子?"我似懂非懂,却趁他转身时把半把麦粒塞进凉鞋缝,幻想明天能长出串麦穗——直到傍晚回家,母亲从我的脚趾缝里捻出三颗发芽的麦粒,嗔怪着说我把田垄搬进了堂屋。
日头爬过老榆树时,父亲把犁靠在田埂上歇晌。我枕着草帽听山脚下传来"叮铃铃"的脆响,像谁把串碎银抛进了竹林。"那是啥?"我踢着土块问。父亲往旱烟袋里按烟叶的手顿了顿:"是学校的钟。"烟锅里的火星明灭间,他指着远处青瓦白墙的院落:"等你手劲能攥稳耧把时,就能去那儿听钟了。"我盯着自己沾着泥的小手,忽然把犁柄当笔杆比划:"那他们上课要不要扶耧?课本里能长出玉米吗?"父亲被烟呛得咳嗽起来,烟圈裹着笑声飘向地头的向日葵,花瓣上的露珠正折射出教室玻璃般的光。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父亲没说完的话藏在犁头的锈迹里——当城市的霓虹替下田埂的萤火,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不出耧车划出的三道痕,唯有山脚下那声铃,至今还在某个月升时分,把埋在掌纹里的麦种,催成回乡的芽。
中午十分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着大地,父亲的脸颊上流着豆大的汗水,我热的实在受不了了嚷嚷着要回家,父亲便让我自己回了和母亲去插秧,回家后的我兴奋不已因为可以玩水了,回家睡了一会儿午觉等着爸爸回来吃完午饭就和母亲一起出发去水田里插秧了。
我光脚踩进水田时,裤管还沾着上午犁地的泥星。母亲递来扎成束的秧苗,青绿色的根须在水中晃出细碎涟漪,像谁把春天的脉络拆成了千万条。"插秧要像拜菩萨,腰弯到能看见自己的影子。"爷爷蹲在前方的水洼里,银发垂落时惊散了水底的云影——他插下的秧苗排成直线,倒影在镜面般的田水里长成另一片青禾,让我忽然分不清哪头是天,哪头是地。
我攥着秧苗往泥里按,指腹刚触到软滑的田泥就猛地缩回——水底的蚂蟥正扭着黑褐色的身子往脚踝爬。"它们也要吃秧苗吗?"我甩着脚溅起水花,爷爷却用秧苗根须轻轻拨开那团蠕动的黑影:"土是活的,水里养着给秧苗松土的虫。你看每株秧脚下都有气泡,那是泥在喘气呢。"我趴在水田里看气泡往上冒,阳光穿过水面时把气泡染成彩虹色,忽然发现每颗气泡里都锁着半片天空,像秧苗在水下种出的星星。
父亲忙完下面的田,正来到了水田的田埂上时,我正把秧苗插成歪歪扭扭的圆圈。"你这是种迷宫呢?"母亲笑着递来野枣,枣汁染红指尖时,我看见自己插的秧苗在风里摇晃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